撰文:CLAY SKIPPER
━━━━━
我今年26岁,单身,四年前刚刚结束一段认真的恋爱。就像其他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,我决定:在我妈的手机上装 Tinder,然后让她帮我约女生。当然,是以我的名义。
仲夏的一个傍晚,走在纽约西村的街上,我马上要见到一个在网上认识的女生。更准确的说,她是我妈假装是我,在她的手机用软件认识的。她用我的 Tinder,帮我安排了这次约会,希望能帮我找到女朋友。我只知道这个女生的名字,在约定的酒吧附近,我见到一个褐色头发的女生站在外面。那一定是她了。
我耳边还能听到我妈几天前说的话。“你说不定会染上很多性病,”她拿着我的电话一边说,一边扫阅着许多撅嘴卖萌的女生的照片。“我觉得你不应该为了上床随便勾搭。你应该好好认识些正经姑娘。”
当我把我的 Tinder 交到我妈手上时,我知道这会很搞笑。我从没想过我们会谈到随便上床的事情,不过我们竟然说了。
“天啊,这儿有一个姑娘很适合你,”她说。“她没穿衣服!妈呀!”
妈妈,Tinder 上不可能有全裸的个人照片。
“嗯,这个不行,淘汰,”她说。好了,一位有可能成为我心灵伴侣的人就这样被放弃了。“你身材好也别这么爱露嘛!”
哦,天哪!
“我有我的考虑因素,”她说。“毕竟我是一个母亲。”
这一切的开始,都是因为我妈觉得我会孤独终老。
或者,至少在上次我们决定一起去看百老汇音乐剧《汉密尔顿》的时候,我自己是这样想的。
“我们有四张票,”她提前几个月告诉我,“爸爸,我,你,如果你到时候有朋友的话,也可以带来。”
“到时候”有朋友?所以,现在的朋友不行?所以,是女朋友咯?你是在说女朋友吧,妈?
我今年26岁,单身四年了。我妈26岁时已经嫁给了自己高中时的男友。当年,也是他开着一辆傻气的甲壳虫载着她去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。28岁的时候,她已经生了第一个宝宝。那个宝宝是我哥,他26岁的时候已经跟现在的妻子谈恋爱了,他们结婚6年了。
所以现在到我了。单身。慢慢死去。每年圣诞节都是那个多出来的人,一个1000瓦的电灯泡。
但是跟我妈26岁的时候不同,现在我们有约会软件 Tinder,当你没人可摸的时候,你可以在 iPhone 上“摸”它。于我而言,Tinder 一直是一个消遣,就像一个成人收费版的“糖果粉碎传奇”游戏。Tinder 并不能让你马上跟谁在一起,但是可以给你创造一种幻觉,让你觉得自己不是自己一个人。它让你觉得,你还有很多机会,可以约很多人,她们其中不少还会想跟你睡。如果我妈那么希望我有个女朋友,那为什么不让她去帮我找呢?所以我把她推上前线,假装是我。
我们在曼哈顿一起吃了顿晚饭,然后我把软件装在她的手机里,教她怎么用,教她怎么速配(还真的当场就找到了一个!),然后把软件从我自己的手机里删掉了。我的感情生活就这样被放在了我妈手里。
她的任务,就是每天花几分钟跟那些“收藏”我的女生聊聊天,再回过头来“收藏”她们。如果她以为一个1米8高,26岁的 GQ 作者的身份能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,并成功约到一个见面喝酒的机会——或者像她建议的那样,去公园散步——她就可以把我的电话给她,然后她们可以给我(我的手机号)发短信,然后我们自己约时间地点。
不过,那是一个大写的“如果”。
我们离开了餐厅,我的哥嫂回到了切尔西区的家,我的爸妈回了康州的家。我自己回家了。
三十分钟之后,我回到家了。我收到了我妈两个语音信息。第一个是晚上9点51分:
“嗨,是妈妈。她(速配的女生)给我回信了。我问她想不想出来喝杯咖啡或者小酌。她告诉我她已经睡了。这是一个信号么?”说罢之后她放声大笑,意思是或者这就是“上床”的暗号,然后她把自己逗乐了。“我给她回短信说,‘也不一定要今晚。’好吧,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我都不太确定是我们选了这个 Alex。是我们选的吗?还是她选的你?随便吧。好吧。拜拜。”
第二个信息是31分钟后:
“我是妈妈,打来跟你说说 Tinder 的回复。我跟 Kelsey 聊了一下。她说,她希望能跟你见面喝一杯。我先问她要不要出来喝杯东西。开始,她说,‘Molly。’后来又说自己是开玩笑的,然后答应喝酒了,说九月份才来纽约。然后我也不知道该跟这些人说什么了。我会给她们俩你的电话。好了。再见。”
Molly?
哦,是那种迷幻药!
我当然不惊讶我妈不知道 Molly 是什么。我惊讶的是,她的风格那么直接,而且竟然那么奏效!她玩得那么好。“我赢咯”?这是妈妈们常会说的话么?我妈真的比我更会玩么?
我给她打了个电话。这离我给她装软件还不到两个小时。
“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应付这些女生?”她拿起电话就问。“我是不是该给你们好好地牵线,还是应该默默地消失。”
默默消失?
Tinder,你是谁,你对我妈做了什么?
我妈今年58岁,短头发,不到1米6,对无app试玩平台排行聊废话零容忍。她生长在一个牧师的家庭,所以我们家的风格也很类似,虽然不算独裁但是也很强硬。她是我们两个男孩的女酋长。如果加上我爸的话,就是三个,她是这么算的。在家里她一直唱白脸,她有特殊的妈妈技能,可以深睡到11点58分,但是只要你11点59分没到家,她就能马上惊醒。她会给我打电话,而我正在赶回家的路上,然后我一接电话,她就会说:“开车的时候不要打电话!”就跟大多数家长一样,她要忍受很多青春期的抱怨,但是却很少获得应得的感激。
当我开始上大学,开始懂道理了,我才发现自己是傻瓜,她才是聪明的那个;我才意识到,她所做的一切只是确保自己的孩子不要闯大祸,那么,既然“在丹家打游戏机”其实意味着我们“在丹家偷他爸爸的酒喝,” 偶尔说说“不”,也是可以理解。即使,这样会让情绪不稳定的青少年觉得你是一个法西斯。既然明白了她一直都是正确的,我开始常常跟她聊天。我会问一些迫切的问题,比如说“我可以把抗生素混伏特加喝吗?不是,我说的是很多伏特加。”或者“怎么把西装上的辣椒酱洗掉? 对,我说的是很多辣椒酱。”
她也会有问题:能告诉我 iCloud 在那里吗?为什么我的 iPod 只能放圣诞歌?
在我的印象中,我们仅有那么一次谈论到了性,当时我22岁,刚刚毕业,我们两个在家里的后院吃饭。她忽然说,“你应该用安全套。”她以为我的性生活很活跃吗?还是完全没有过?我默默地换了话题。
(备注:在我给我妈看过这个故事之后,她写到:“我觉得肯定是在你高中和大学的时候,我们就说过安全套的问题了。并不是到了22岁才聊的!”请注意,“觉得肯定”跟“肯定”是不一样的。)
四年后的今天,她在帮我进行网上约会。
在她给我转发的短信中,我不确定哪些因素让我最不舒服:是收到许多垃圾短信(“一看就是嫖妓广告”,她说);还是她为了吸引女生用“抱负远大的文字工作者”来形容我;还是老妈对从事 HR 工作的女生特别热情,因为她要 “帮你扩大社交网,谁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失业!”这件事情。我妈妈真的长期处于一种担心她儿子会被炒鱿鱼的状态么?还是她真的那么讨厌写作?
我已经把软件从我的手机上删除了,所以我现在全靠我妈用短信给我汇报进展,而她的短信,常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黑体字,让我仿佛听到她在我耳边大叫:
“很多配对不成功。很多都很年轻。有一些年纪大些。有一些太爱晒胸了。”
“我不确定我是不是个很光滑的男人,我不是在约泡。”
看看她的短信,就能发现,虽然她很熟练地使用一些流行词,比如说“赢你咯”还有“默默消失”,她离得心应手还远着呢。
她会跟女生说,我们好像有很多共同之处,你认识谁谁谁和谁谁谁么?女生说,认识,我们是高中同学。她便说,那我们在同一个高中呢!女生说,我是2007届的。她说,我是2008届的。女生问,那我不是吃嫩草?老妈会忽略这个问题然后说,我哥哥跟谁谁谁的哥哥是好朋友。
如果发现有女生也来自康州,在我家附近长大,她还会自我介绍说:我妈妈在市区的书店工作,而且经常去那里的体育馆健身,还会去逛有机超市。
我问她,你真的觉得这些对话能撩妹吗?
“我的 Tinder 信息是用来跟女生好好交流的,不是用来撩妹的!”
于是它们确实开展了对话,至少有时候奏效吧,虽然那些对话都是关于我已经忘记了的高中同学,或者关于我妈的工作地点,健身房,有机市场等等。不过一段时间之后,她开启话题的能力越来越娴熟,不过她还是没有给我约到女生。我觉得老妈的主要问题如下:
首先,她有时候说话像个机器人。
有个女生说自己在国庆日“为美国而玩得太疯了”,所以伤了膝盖,并且提到纽约实在不适合有出行障碍的人生活,我妈的回复是:“赞同该城市不适合骨折人士出行。”(她还问,“你是运动员么?”还有“地铁有直梯么?”)
再有,她不是很有游戏精神,也就是说,她从来学不会放轻松。
“我不能一次问两个问题吗?!”当我告诉她不行,真的不行的时候,她很质疑。“这不好么?为什么?或许我应该问三到四个问题!’你住哪里?你做什么?你养什么动物?你喜欢长袖子吗?‘”
(后来,她给我发短信说:“在问完昨天的问题后,我没有收到回复!看来确实不应该一次问两个问题。”)
事情真正变得失控,是在她读了一篇《名利场》上关于 Tinder 的文章之后,里面谈到了当下的勾搭文化,还有这句耸人听闻,太完美以至于难以置信的话:“‘约炮就像用订餐软件一样,’投资银行家丹说。‘不同的是你预订的是一个人。’”(谢谢你,投资银行家丹。)
“那这不就是约炮网站咯???”她读完文章之后发短信问我。“我可不玩这个!”
这就是把你妈妈推上前线,去面对一群想跟你睡觉的人的后果:总有一天她会告诉你你心知肚明的事情,而这会让你很不舒服;她免不了用一种妈妈的语气劝你,再跟你说,你也知道,性不是一切。
“性不是一切,”她说。“亲密是亲密,性是性。亲密是用善意好好地对待别人。轻轻地拍他们的背,或者握着他们的手。除了睡在一起以外,还有好多事情能把你跟另外一个人连接在一起。”
是的,好的,妈妈。难道你以为我们这代人真的不懂这个么?
“我不确定你真的懂,”她说,显然,用了一个星期的 Tinder 已经让她很倦怠。“我不知道人们还是不是接受这样的教育。或许这种想法过时了吧。”
我的爸爸妈妈是在高中认识的,当时他们一起负责制作毕业纪念册。她开始没留意到他,直到有一个雪天,他开车送她回家。而这一天变成了他们的约会日,一起去看《美国风情画》,吃甜甜圈,接着便是结婚,在接下来便有了我。
$$$app试玩平台排行$$$“以前,人们都是面对面认识的,”我妈后来说, 为人们寻找真爱消除了物理距离是互联网创造的几大奇迹之一,可却让她哀叹。“在工作的地方,你会见到他们,或者在俱乐部,在学校,在教堂…...你们总会有些共同点,然后常常见面,接着就会想,‘我喜欢他们么?他们是混蛋么?’而不是像这样:哦,我发这张图,我喜欢那张图。接着就是:哦,他们喜欢我!然后你们聊什么呢?”
“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住在纽约?”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根本不在纽约的人,这真是讽刺。“不过,我想今天的世界就是这样吧。”
我问她:你会觉得你的20岁里没有 Tinder 很可惜么?
“我不会。绝对不会,”她说,这对我爸来说绝对是好消息。“不过你要记住,Clay,我长大的时候环境并不一样。当时就是不一样。”
康州的清晨,我的中年的妈妈坐在家里,用手机给她的小儿子发 emoji 的表情(我妈!用 emoji!),讨论女朋友的问题,亲密的问题,还有好多其他我们以前不聊的话题。从某种角度来说,我们的沟通变多了。这确实不一样。
有进展了。
几天之后,我妈摆脱了《名利场》带来的小烦恼,终于给我安排了一场约会。在 Tinder 上聊了很久之后,她帮我约了一个褐色头发叫 Anna 的女生出来喝一杯,还把我的手机号给了她。她给我发了短信,我们约在西村的一家酒吧。我到的时候,她已经在等了。
Anna 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不过她显然是我妈妈喜欢的类型。(我想,至少我们这点是不一样的)我主动拥抱了她一下,说:“你好,很高兴见到你,”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互动,当然她是不知道的。
约会很糟糕。我们除了都有一双眼睛和一份工作一样,什么都不一样。我们一起呆了一小时,各自喝了两杯酒。如果我有问到任何我们在 Tinder 上已经讨论过的问题,她倒是没有告诉我。我的计划本来是告诉她,其实一直是我妈妈在用我的 Tinder。但是很快我的良心让我退却了。我意识到很多人确实是用软件来找新朋友(也有成功的!),我觉得如果跟她说出真相“其实喜欢你的是我妈”是一件很伤人的事情。约会结束了,我们各回各家,完全没有性的事。
我后来问我妈,她选择对象的标准是什么。我想要知道她选择 Anna 的原因。
“我就看看谁长得好看,但是又稍微有点内涵,而不是一副只想上床的样子,”她告诉我。“我会跟她聊天,然后邀请她喝咖啡,或者约在公园。所以我会喜欢那些喜欢跳伞的,滑雪的,和玩长曲棍球的。或者还有那些养狗的。”
不过当然,这个实验本来也是有些荒唐的,想达到目的几乎是不可能的。(“我觉得光用手指扫来扫去,你是不会找到真爱的,”我聪慧的妈妈说。)这本来就行不通,所以事实也如此。
《汉密尔顿》音乐剧近在眼前,而那第四张票到了我朋友 John 的手里。他不是我女朋友。
当这一切过去几个礼拜之后,我重新下载了 Tinder,为了写这篇文章,我想找找我妈和 Anna 对话,可是却找不到她了。可能她删除了软件,或者在完美的因果报应链中,我“默默被消失”了。
我想到,从 iPhone 软件里跳出来,回到现实世界,在2D和3D生活中来来去去,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情。我想起我的爸妈。我在想,当你有那么多人可以“收藏”进你的生活,你是会留意那个下雪天开车送你的纪念册小伙子,还是坐在他的车里,扫阅着那些饥渴的陌生男人的照片?我在想,你会不会因为总在寻觅而错过一些人。
在我妈帮我在网上找女朋友未遂之后,我和一个认识了一年的女生朋友开始发展。她叫 Katie。她今年30岁,有真实的脉搏,而且从来没上过 Tinder。(我们原来就认识,后来通过 Twitter DM 又联系上,这个浪漫软件我妈肯定还不会用。)我们是异地,还没约会,不过会尽可能跟对方见见面。我们对现状很满意,也不想定义这段关系。我跟 Katie 飞去巴哈马过圣诞节之后,我尝试着跟我妈解释这段关系,她不太明白。我奶奶问我,我的新女朋友怎么样,可我还没有女朋友。我想,我们确实在不同的环境下长大吧。
最近,Katie 和我在西村吃饭。餐厅很拥挤,弥漫着纽约城周五的躁动气息。我们坐在吧台,有一个醉醺醺的女人从 Katie 背后靠过来。
“你们俩会结婚的,”她说。
这句话是极其不成熟的预言,毕竟我们甚至没在约会。但是我好奇地问她:那你说,我们的故事是怎样的?你觉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?她又再靠过来。
“你们在 Tinder 上认识的,”她立马说,因为这是2016年,如果两个年轻人看起来快要结婚了,那显然他们 是在手机上认识的。
Katie看着我,我们俩都笑了。我们结了账,然后走过那些享受着烛光晚餐的情侣。我走了两个街区,回到我家,再也不是自己一个人了,我心想,天哪,我得回去给我妈发短信。
━━━━━
撰文:Clay Skipper 翻译:Elyse Huang 插画:徐磊、Tara Jacoby
━━━━━


 相关文章
相关文章




 精彩导读
精彩导读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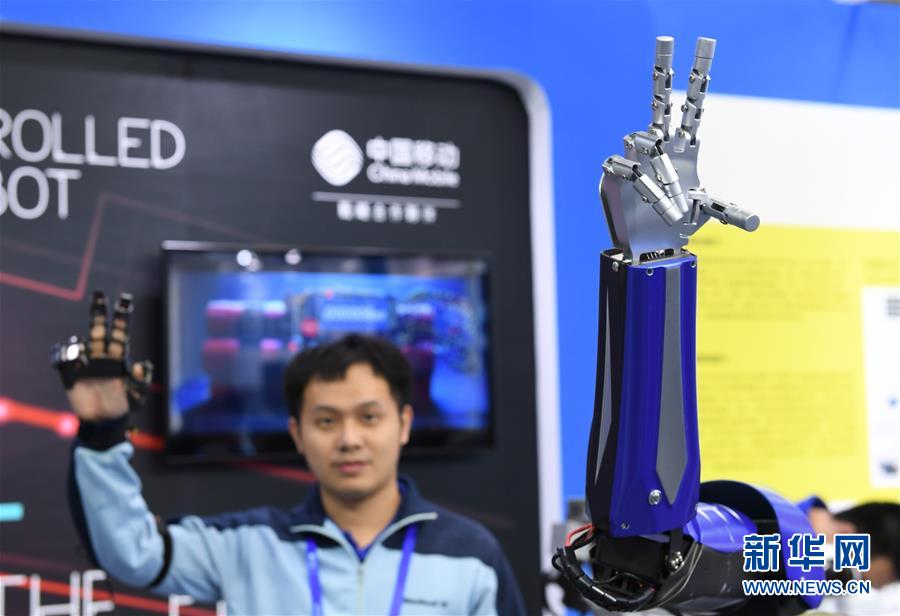
 热门资讯
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
关注我们
